

我出生在陜北一個山高溝深的小山村,一條小河穿村而過,村民們世代沿小河兩岸的山坡掏窯洞而居,村子里最紅火的時候住著600多人,是遠近聞名的大村,改革開放后,進城務(wù)工做生意上學(xué)的人多了,村子里住的人越來越少,最近這兩年,偌大的一個村子只住了不到十個人,還都是年齡大的,以前的熱鬧場景再也見不到了。村子里人少了,牲畜也就少了,種地的都開著三輪摩托下地干活,野生動物越發(fā)的多了起來,石雞、野雞滿山飛,野兔、野豬、狐貍鉆溝上峁到處跑,每逢清明、中元、冬至,城里居住的人都拖家?guī)Э诘幕卮迳蠅灍埣赖熳嫦龋@幾天也是村里最有煙火氣的時候。
幾年前,撤村并村后,周邊的8個村子合在了一起,以前的村民委員會變成了村民小組,村里今年換屆選舉,新當(dāng)選的村委會副主任和村民小組組長新官上任三把火,舊事重提,再一次把修建村民小組活動室的事提上了本屆班子的工作日程。幾天前,村子里召開村民代表會議,就村民小組活動室修建事宜進行協(xié)商,我作為書記員參加了會議,會上就村民活動室選址和新農(nóng)村建設(shè)的有關(guān)事項進行了充分的溝通協(xié)商,市鎮(zhèn)兩級有關(guān)部門也給予了充分的支持,基本達成了統(tǒng)一意見。當(dāng)天晚上散會后回家,六歲的兒子在電梯里問我為啥要修新農(nóng)村,我給孩子解釋說為了能有個家啊,兒子又說我們不是有家么,我又解釋到城里的這個是家,村里修建的是根,是讓我們知道從哪里來的一個地方,是真正的家。兒子再說根是啥?我再解釋,根就是一個人來的地方,爸爸出生在那個地方,是吃著那個地方的食物喝著那個地方的水長大的,對爸爸來說,爸爸的根在村里,爺爺奶奶的前半生都留在了那個地方,家里的祖輩們都埋在那個地方,那個地方就是家,不論我們住在哪兒走到哪兒,根不會動,始終還在村子里。兒子似懂非懂的說,我的老奶奶就埋在那個地方,老奶奶就是我們的根,我笑著說對,你的根也在村子里,在黃土地里,我們所有人的根都在土里,土地給予了我們一切,吃的喝的用的都來源于土地,所以我們要感謝土地,你的名字里有個“ 植 ”字,希望你能把自己的根“植”在土里,不忘來路,勇往直前。
找到自己的根,滋養(yǎng)自己的根,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其實很難。秋末冬初,小區(qū)院子的美國梧桐寬大的葉子開始掉落,梧桐的葉柄有特殊性,落葉跨越的時間比較長,從秋末一直到第二年春天的新葉萌發(fā),葉子掉落在路面上,環(huán)衛(wèi)工人會每天進行清掃,清掃收集的樹葉會被垃圾車收走送到垃圾集中填埋場進行填埋,“葉落歸根”對梧桐樹而言是奢望,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扎根開枝散葉,好不容易立在了一個地方,葉子找不到根,葉子回歸不了滋養(yǎng)自己的土地,回家的路漫長而艱辛。梧桐尚且如此,何況乎吾輩,抬頭三尺是遠方,地下三尺是故鄉(xiāng)。父母在年輕的時候從未想著有一天能離開村里,走出大山,費勁的在村子南頭平整出一塊宅基地,父親更是雇了一輛推土車,整整一個月的時間,推出了一塊可以修建一排窯洞的平地,母親在宅基地旁修梯田、打水壩,汗水和心血都傾注在這塊宅基地旁,宅基地和梯田上種植果樹,父親從縣城農(nóng)藝所淘換的新品種,豐水梨、香蕉梨、鴨梨、水蜜桃、蟠桃、黃元帥蘋果、國光蘋果、花牛蘋果等都是村民不曾見過的稀罕物,母親精心侍弄,不幾年就掛果了,種的多自家吃不了,母親就借上鄰居的牛車逢集必趕,在集市上售賣,一斤不過五角,母親還種了幾架葡萄,那些年我們兄弟幾個水果總是管夠吃,不再整天惦記村里誰家的果樹上的果子了。推出了宅基地,母親又張羅著燒磚箍窯,村里不產(chǎn)沙子,就從十里之外的另一個村子拉沙子,自家沒有牛車,就借用親戚家的牛車,和泥制胚拖胚,都是自己親自上手,雇的一個燒磚師傅,總計燒了三窯青磚,燒好的磚從磚窯拉出整齊的碼放在宅基地上,箍窯的材料都準備齊了,就等著動工建設(shè)了,可這一等就是近三十年。
又過了幾年,我和弟弟進城讀書,母親也跟著進城陪讀,家里起先住的祖輩傳下來的兩孔窯洞也被遺棄了,再也沒有住過人。兩孔窯洞坐北面南,是陜北人說的人字窯,窯坐落在村子的正中間,兩條小河夾院而流,窯洞的院子里種了一棵梨樹、五棵棗樹,一個磨盤立在梨樹旁,院墻跟前有洋槐樹數(shù)棵,粗壯而高大。院墻用石塊壘砌而成,最上邊夯土,奶奶在墻頭上種了幾株澤蒙花,院門是磚木結(jié)構(gòu),上覆青瓦。窯洞進深6米,主體是石頭箍出來的,西邊的窯洞里邊土炕的里邊還套著一個進深4米多的土窯洞,土炕的東邊還套了一個存放衣物的小窯,一主兩副,極為實用。夏天的時候,只要把最里邊的土窯洞的門打開,睡覺的時候還要蓋被子,冬暖夏涼都不足以形容祖輩的穴居智慧。我對這兩孔窯洞的感情極深,始終無法割舍,至今偶爾還在夢里回到窯洞里,躺在土炕上,聞著土灶上柴草燃燒的味道,愜意的享受著歲月靜好。我出生在西邊的那孔窯洞里,在窯洞里度過了最快樂的童年時光,記憶里,母親總是圍繞著灶臺和十幾畝坡地轉(zhuǎn),腳踩著黃土,背靠著黃土,我會走路后也整日和黃土為伴,玩泥巴,跟母親下地種種子,收秋撿拾谷穗土豆,對土地的感情之深,融到了血脈中,鐫刻在骨子里。院子里用石頭砌了一個露天的灶臺,春夏秋季做飯就在院子里,春天的時候,我坐在灶臺前,用力拉著風(fēng)箱,不停地給灶臺里填柴火,頭頂?shù)难蠡睒湔_著槐花,花香滿園,蜜蜂飛舞,鐵鍋里咕嘟咕嘟的吃食散發(fā)著誘人的香氣。夏天的時候,日子悠長,母親在地里勞作的時間也長,晚飯往往到了太陽下山后才開始做,我盯著灶頭的紅彤彤的火苗,用力的拉著風(fēng)箱,期待著飽腹的那碗飯早點做熟,周圍山頭上的貓頭鷹早早的開始了哀嚎模式,一聲聲的叫的我心里發(fā)憷。秋天的時候,我會推著磨盤一圈圈的轉(zhuǎn),新打下來的黑豆被沉重的磨盤一點點磨成豆?jié){,豆?jié){熬煮在灶頭的大鐵鍋里,鹵水點豆腐,豆香四溢,蘸著陳醋和切碎的紅蔥沫吃,口齒生香。
從小推磨盤,我長大后對磨盤倍感親切,偶爾想起磨盤,就想起了我的團團轉(zhuǎn),仿佛有一根繩子拉著我不停的在打轉(zhuǎn)轉(zhuǎn),繩子不斷,牽掛割舍也就不斷。離開村子近三十年,兩孔窯洞也被閑置了三十年,村子里打壩攔洪,壩基越來越高,壩地面積逐年增加,現(xiàn)在已經(jīng)延伸到和老屋院子一樣平了,窯洞的松木門窗早就散架了,窯洞內(nèi)壁的泥皮也全部脫落光了,靠東邊的窯洞墻體垮落,窯洞已無法住人。里邊的舊家具、黑瓷甕等被跌落的泥皮覆蓋,舊物件散發(fā)著土腥味、霉菌味,前兩年我和弟弟回村的時候還鉆進窯洞里把多年未動的東西翻騰了一遍,找到了好幾張舊照片,還有一些喚起我們回憶的小物件。也許這是我們最后一次進到老屋里了,日子緩慢的流淌,村里要修新農(nóng)村的提議被村民采納后,選址起先就定在了我家老屋的那個地方,計劃著整體推倒加高后進行建設(shè),我最先想到的是要把兩孔窯洞中間窯腿位置的天地窯完整的取出來,這個天地窯鑲嵌在兩孔窯洞之間,細石面整體雕刻,高一尺有余,左右還雕刻了一副對聯(lián),留下了這個天地窯,也算是能留下點關(guān)于老屋的念想,把牽連不斷的那個繩子留下來。
每次回村,我們弟兄幾個都要去父母付出汗水拓而未建的宅基地走一遭,沿著曾經(jīng)無數(shù)次走過的那條土路款步而上, 沿路有村里種植的一顆山楂樹每年都掛果,無人采摘,歡喜了周邊的鳥兒。周圍母親早年種植的果樹早已死的死、荒的荒,特別是桃樹全部都死了,葡萄每年地面部分的枝干被冬天的冷風(fēng)吹干,第二年春天有冒出新枝條,循環(huán)往復(fù)。像被刀切了的土楞上酸棗樹向陽而生,宅基地旁母親早年為固土栽種的棗樹長至一胳膊粗,溝地的旱柳長得分外茂盛,野兔子、野山雞一躥而過,高壘的青磚被風(fēng)吹的散去了青色,顯出了灰色,磚塊上鳥糞隨處可見。踩在土里,噗嗤噗嗤的聲音,黃土更細了,坐下來,看著對面高高的那個山頭,山頭下是一塊兒坡地,母親當(dāng)年帶著我和弟弟在坡地上刨土豆,曾經(jīng)挖出來一個磚塊兒大小的土豆,我抱在懷里從村前溝走到家里,逢人就炫耀,仿佛從土里刨出了個大金疙瘩。
雖然土地里長不出金疙瘩,土里長不出白面饃,土里刨出的吃食僅僅能讓我們不餓肚子,可我們從未對這片土地有一丁點的嫌棄,我們無比熱愛腳下的這片土地, 想著有一天我們能葉落歸根,回到這個地方,平靜安詳?shù)脑嵊谝徽牲S土之下,子輩們能夠記得他們從這里來,不論以后走的有多遠,記得根在的地方。
奶奶去年走了,從黃土地里來,又回到了黃土地。她生前總是記掛這那兩孔窯洞,記掛這她侍弄了一輩子的那十幾畝土地,嘴里念叨著村里的人、窯洞、樹、山路,村子的每一塊兒土地是誰家的,那個溝道里那顆樹是誰家的,那個坡上埋的誰家的先人,這些都記得清清楚楚。陜北人愛吃燉菜,甚至很長時間的烹飪手法就是燉和蒸,古人的鼎食就是燉煮,至今所有的陜北媳婦都能拿手的做上一頓燴菜,這與我們尊重食物、珍惜食物有很大的關(guān)系,燉煮的時候,食物的香氣隨著蒸汽上升,從土里來直達天庭,氤氳朦朧,仿佛早已遠去的先人能和我們一同享受這食物的美好。幾次給奶奶上墳燒紙,看著青煙扶搖直上,青煙在這一刻連接了地下、地面、天上的所有人,思緒遠去飄散。
兒子一天天長大,能吃能耍,身體壯的像一頭牛,完成了他的老奶奶曾經(jīng)的愿望,成為家里的壯“ 勞力 ”,每次他一說起他的老奶奶,我就眼淚止不住的流,孩子畢竟還小,對生死的理解沒有我們透徹,思考的少,憂愁就少,快樂自然就多,但愿他有一天能夠明白父輩們對根的執(zhí)念,完成父輩們對根的最后渴望。
路長且艱,愿你我都能葉落歸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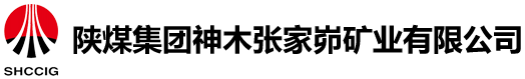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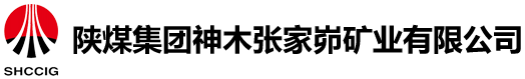

 發(fā)布日期:2023-02-10
發(fā)布日期:2023-02-10
 點擊量:1723 作者:劉波 來源:
點擊量:1723 作者:劉波 來源: